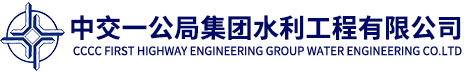193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冀朝鼎用英文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此作奠定了冀朝鼎的学术声誉根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评价说:“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水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当然也是中华经济历史发展的重要纽带。在这本著作中,冀朝鼎论证了中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辩证地阐述了黄河流域的土壤侵蚀、海河流域的开发、江南围田的利用及山区土地的利用等,并以中国统一与分裂作为研究对象,开拓性地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个重要概念: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个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有可能统一全中国。
水利的“杠杆效应”
历史上,水依次主要表现为三大功能:一是人畜饮用;二是农田灌溉;三是交通运输。至少在19世纪中叶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国门之前,农业生产一直是历朝历代“政治与军事力量的衡量尺度”。越是传统的农耕活动越得看天吃饭,对于水以及水利的依赖程度也越高。正因如此,中华文明的水利发展历程与农业发展史息息相关。在长期的农业时代,农业当仁不让地扮演着经济社会主力军角色,因此,水以及水利的变迁实际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冀朝鼎将公元前255年至1842年的中国经济史划分为5个时期:公元前255年至公元220年的秦汉两代为第一个统一与和平时期。那时,以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为其基本经济区。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的三国、晋、南北朝,是第一个分裂与斗争时期。在这一时期,因为灌溉与防洪事业的发展,四川与长江下游逐渐得到开发,因而出现了一个能与前一时期的基本经济区所具有的优势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公元589年至公元907年的隋唐,是第二个统一与和平时期。此时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大运河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将首都与基本经济区连接起来了。公元907年至1280年的五代、宋、辽、金,是第二个分裂与斗争时期,长江流域作为中国显著的基本经济区有了进一步充分发展。元、明、清三代,则是第三个统一与和平时期,统治者们对于首都与基本经济区相距太远而犯愁,多次想把海河流域发展成为基本经济区。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冀朝鼎从历史分合规律中发现了水利的“杠杆效应”。统一与和平时期,水利建设在地理上与统治集团较近,便利交通有助于统治集团集中资源,农业中心的发展有助于巩固统治利益。如秦通过改造泾水、渭水发展关中农业。隋唐包括元、明、清,其政治中心虽居北方,但发达的运河交通,将长江与黄河地区的农业经济汇成一片,方便资源集中。相比之下,分裂与斗争时期,常常是远离中央的地方得益于水利建设,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终有实力同中央集权“扳手腕”。如蜀国地处四川盆地,水源充足,农业发达,地理上又易守难攻,所以面对兵强马壮的蜀国,魏国颇费周章。
正是由于一些地方水利蓬勃发展,为基本经济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而有机会撬动既有力量格局,进而影响中国的分离与统一。或者说,谁掌握了这些基本经济区,谁就拥有了统一中国的潜在实力。
水利被权力化后的角力
《吕氏春秋·慎人》曾曰:“掘地财,取水利。”东汉高诱对“水利”二字的注释为“濯灌”。不难看出,水利最初仅是表达灌溉之意。灌溉受制于水源供给,而水源总量有限,矛盾在所难免,中外历史上均不乏因水源争夺而引发的“水战争”案例。
虽然江河湖泊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冀朝鼎研究发现,同为水利,西北的水利更多突出农业灌溉功能,而黄河、淮河和长江中下游的水利,大都以防治水患为主。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据考证,“从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155年间,大水灾就发生了1029次,几乎每两年就有一次”。而“明代时大河(黄河)北决者有14次,南决者5次。清顺治康熙以来,黄河北决者19次,南决者11次”。钱穆先生发现,“黄河的大水患多在宋以后”,之所以经常溃决,全因“不能按其自然趋势以定流向”。
实际上,屡遭黄河水患之苦的历代百姓,多次兴修水利,试图治理水患,但在河道走向上的探索颇多曲折,这既有对自然认知的局限性,也夹杂进战略这样的军事意图。宋仁宗八年,商胡决河后分成东、北两支。对此,“宋代人主张河水东流,可作防敌的国防线,北流则流经契丹,认为对宋不利”。
类似把水当成战争武器的现象屡见不鲜,最为常见的诸如大小城镇必依城墙而挖的护城河。战国时期的郑国渠虽为秦国在诸强中率先强大做出重大贡献,但此工程初衷原不过是韩国的“疲秦”大计。
知名史前史考古学教授、英国最高学术机构不列颠学术院院士史蒂文·米森通过考察发现,水在人类历史上实已被“权力化”:统治集团以此来强化统治力量,上层社会以此来突出地位,强国借助水利赢得战争。
水一旦被“权力化”,自然会开发出许多用来制衡敌方的新功能。水利于是不再仅具促进经济社会建设的和平意义,同时兼具抗衡敌国的军事使命。兴修水利也不再只是单纯有益于百姓的大好事,因为水利工程过多过滥,必定会加重百姓负担,当负担不断累积而无法释放时,自然对统治者构成威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便是此道。
应“水”而生的经济区
按钱穆先生的看法,“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早懂得水利的民族”。冀朝鼎认为,“在中国的每个地方,灌溉是集约农业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便确立了中国的农业社会”。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郑国渠、都江堰等著名水利工程。不过,对久负盛名的大禹治水传说,冀朝鼎经过严谨考证后认为,只是个被反复移植拔高了的民间传说。这个传说之所以为历代所笃信,主要在于“统治者认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开端,要归功于一个英雄神灵的传递和他的自我牺牲的活动”。在农耕时代,兴修水利虽然大有裨益,但这样庞大的工程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长时间投入,这势必影响百姓群体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封建统治的稳定。大禹传说的存在,就像是统治者为水利工程寻找到来自“天命”的正当依据。
治住了水,农业发展便有了较好的根基。农业发展有了基础,地方经济自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正因如此,无论是位居庙堂之上的明君,还是达官贤臣,对于兴修水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认识极其深刻。绝大多数水利工程建成后,不仅使百姓大大减少水患影响,还带来了农业经济的蓬勃发展。
应“水”而生的本质是顺势而为,在认识自然中顺应与改造自然,这是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大多数朝代赖以发展壮大的重要表征。隋唐接力建设运河,并派生出漕运和依运河而建的粮食储备制度,至于水上交通运输更不必赘言。显而易见,明代的“海禁”当属违背用水规律的反例。
回溯中华历史,水利之于冀朝鼎笔下的基本经济区不单局限于经济学范畴,更像是一部治世之史。